没含泪吃过面包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作者: 发布时间:2008-06-05 15:54:18
浏览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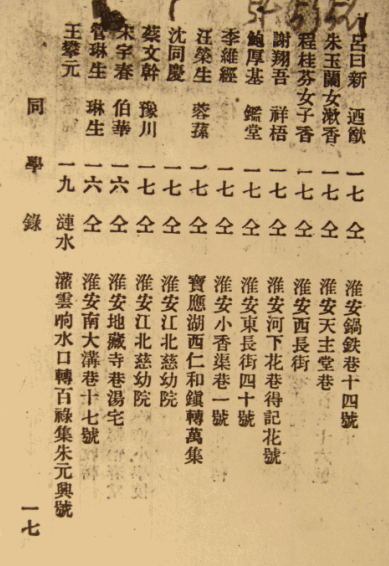
王攀元年谱
1912 江苏世家子弟。
1914 父亲过世。
1924 插班小学四年级,在此之前受教于私塾,闲暇时以毛笔画画自娱。
1926 母亲辞世。考上淮安中学,却无法入学。
1927 正式入学淮安中学。
1930 直升淮安高中部。
1933 考入上海美专西画系。
1936 感染伤寒,住进上海红十字总医院。巧遇国立音专季竹君。
上海美专毕业和季相约赴法国留学,回乡筹款。
1937 卢沟桥事变爆发,滞留家乡。
1946 春天至镇江,于丹阳中学任教一年。
1947 至上海,因时局动荡,只得住到难民营。
1948 与倪月清结婚。
1949 六月携眷来台,落脚凤山。
1952 秋天至罗东中学教书。
1961 与七、八位画友组成“兰阳画会”。
1964 在文艺营上认识李德、庞曾瀛、刘煜、刘其伟等画家。
1966 首展于台北国际画廊,32幅水彩,全数为外国人收藏。
1969 获选全省特殊优良教师。
1973 自学校退休,全心投入绘画创作。
1979 应邀至宜兰青年社团活动中心教授国画,每周一次,持续七年之久。
台湾省立美术馆典藏作品。
台北春之艺廊画展。
1983 荣获中华民国画学会金爵奖。
参加台北市立美术馆开馆展。
于名人画廊展出水彩作品。
1985 参加第一届“亚洲国际美展”于韩国,迄今已臻十六届。
1986 第一次水墨画展于雄狮画廊。
1987 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个展。
台北皇冠艺文中心个展。
1988 参加台湾省立美术馆开馆展。
1989 参加全国美展、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当代艺术发展展”。
1990 台北亚洲艺术中心个展。
1991 台湾省立美术馆第二次典藏作品。
1992 台北诚品画廊个展,并出版画册。
1993 台湾省立美术馆个展,台北市立美术馆典藏作品。
1994 台北形而上画廊“孤独原来不寂寞”个展,并出版回忆录《老天爷的剧本》。
1996 台北形而上画廊“不只是孤独”个展,并二版《老天爷的剧本》。
1997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特展(形而上画廊)。
2001 于国立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举办“攀圆追日-王攀元九十自选展”,并出版《攀圆追日-王攀元自选集》。
台北形而上画廊举办“九个太阳─王攀元精选展”,并改版《攀圆追日─老天爷的剧本》。
荣获第五届国家文艺奖。

创作理念
没有含泪吃过面包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一个画家必需要有自己的体系与风格,那就是孤独。
2001年第五届国家文艺奖 美术类 / 王攀元 得奖理由
王攀元先生为一位内省的艺术家,一生坚苦卓绝,始终执着于绘画创作。自一九四九年来台,在艰困的环境下,持续创作五十余年,在当今众声喧哗的时代,始终自我观照,以细腻深邃的情感诠释简洁的主题,在台湾特定的时空下,呈现出独特精炼的风格。
第五届文馨奖银奖王攀元(资深画家) 得奖感言
我的一生经历充满感动与感激,虽然早年的颠沛不顺遂,更加肯定了我选择艺术这一条路,在艺术的领域中,我在孤独中找寻到生命的泉源。每当我站在画作前,情感的动能从心中延烧到画布,无需太多艺术理论的诠释,情绪心跳便随着笔触色彩舞动起来,我想这是一种直观的解放吧!每当在创作时,我就会陷入一种不由自主的苍茫与深深的迷惘之中,总觉得有一股摆脱不掉、无端的哀愁袭入心中,也许这是经历人生每个阶段的磨难所产生的苦痛,及想藉由画作抒发的情感吧!
公元1912年我出生于江苏豪门,但因童年失怙,在大家族中倍受排挤,王牌坊的奢华富贵于我如池中之莲,只可远观,不能亲炙,求学的过程更是坎坷,在大家族的反对中,我执意进入上海美专的艺术殿堂,实现艺术的梦,但自上海美专毕业后,物质与精神生活并未改善。
1949年带着妻子来台,1952年前往罗东中学担任美术教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宜兰也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1973年我的健康状况不佳,儿女也已长大,我申请退休,并投入更多时间心力于绘画上。1987年我应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邀请举办生平第一次重要的回顾展,接着许多画廊与博物馆也陆续邀请我展览,我真的很感谢各界对我的肯定,我更高兴有机会藉由艺术传达我对这块土地的感情,我想我能传达的除了绘画,还是绘画,毕竟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艺术。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各界及家人让我有机会圆我艺术的梦,尤其是行政院文建会、国立历史博物馆及肯定我的社会大众。
艺术家素描 文/李立亨
“想起过去的种种,彷彿象是黄梁一梦。”王攀元在宜兰家中微笑地说着:“得奖这件事也象是黄梁一梦。”
因着“国立历史博物馆”今年五月所举办的“攀圆追日──王攀元九十自选展”,许多美术爱好者彷彿发现出土文物般地惊艷于王老画作的魅力。因着“国家文艺奖”的颁发,相信会有更多人发现这位与民国同寿的艺术家,他的生平与作品一样动人。
资深画家刘其伟常说:“老天爷早就把剧本写好了”,王攀元拿到的却象是其中最伤心的一本。然而,老画家却没有将太多力气放在丧气与悲伤上面,中刈骰⑸罘彩辍!拔业纳硎雷钔纯啵钇嗖遥辉固煊热耍环⒗紊В也恍沤蹋闹杏刑炖怼!蓖跖试陀讶苏饷此怠�
“天理”让九十高龄的王攀元可以持续读书、写作、生活,而且到今天仍能继续创作比人还高的一百号大型画作。
红苹果的故事
王攀元出生于江苏北部的徐家洪,五进五堂的大宅门前有座宏伟驰名的王家节孝牌坊,宅第内有荷塘杏林与穿梭曲折的回廊,府内所拥有的珍奇古玩更是不胜其数。然而,王家三位少爷的老大与老二都英年早逝,庞大家产的争夺战,在大房二少爷王攀元丧父之后就持续地上演着。
“我三岁父亲去世,九岁的时候就有自知之明,内心经常有一种恐怖感──也就是没有安全感,在睡梦中时常哭叫起来。”王攀元在年初发表的〈浮生往事〉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这么写着。“母亲时常问我,为什么在夜间哭泣,不安何故?我说在睡梦中有人要害我,我很怕!想不到真的,我的一生均在‘怕’字上过生活。”
不仅是王攀元“怕”,王攀元的母亲也“怕”,她既迎战不了大家族复杂人事的波涛汹涌,更在动辄得咎的家规底下饱尝脸色与指斥之苦。为了让小孩不要从小就得看人脸色,母亲只好做些女红与卖点鸡蛋来为小孩挣零用钱。原本应该欢天喜地充满童真的孩提时代,王攀元和母亲一起在被大家庭所漠视和排挤当中渡过。
王攀元记得小时候,三姑买了十几个红苹果回来,他看了好欢喜,忍不住拿了一个兜在怀里拿回房里。母亲发现之后,惊慌得要他赶紧拿回原处免得招惹麻烦。小王攀元哪里知道大人世界的纠缠险恶,只知道自己好喜欢红苹果的鲜嫩颜色与美味。母亲一边落泪一边好言相劝:“等你长大了,成人了,站起来之后,想要苹果还会难吗?”
一直到今天,王攀元对于“红苹果”还是充满着感情。知道王攀元坎坷往事的朋友学生,也总是在拜访王老的时候记得把红苹果也带上。
王攀元最早开始画画是四岁的时候,看着墙上挂着的八大山人等人的真迹顺手也画了起来。进了私塾,闲时就以毛笔作画写字。十三岁,王攀元参加学校美术比赛得了第一名,画的就是“红苹果”。那一年,相依为命的母亲撒手西归。往后学校生涯所延伸的学费问题,王攀元得开始独自去面对叔叔婶婶的冷言冷语。至此,连家里佣人都可以仗势欺负恐吓他。
到底你是不是哑巴?
小学毕业之后,王攀元一举考上江苏的明星学校“淮安中学”,长辈的意思却是要他放弃唸书的念头。僵持了一年,王攀元最后还是在家中佃农的协助之下,才得以离家就学。
王攀元非常珍惜离家住宿在校的中学生活,一九六八年还曾在日记里这么写着:“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内心的思想总有一些超时代的自居,有些看法与想法,似乎与一般同学不太一样,平时沉默寡言,倔强好胜,不与人交,除了读书而外,时常一个人坐在校园里梦想,梦想中来世如再为人,永享父母之爱;梦想中,如有一个真正爱我,柔情似水的女人,一同读书一同作画,一同死去,一同埋在土中永远安息,不再像一个飘零无依的落叶了。由于我个性爱静,又沉于想象,从前如此,现在亦复如此。”
王攀元的沉静寡言,让同学认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自闭者,连训导主任有次都忍不住问他“到底你是不是哑巴?”幸好直升淮安中学高中部之后,美术老师吴茀芝无意中发现他的美术天份,持续鼓励他朝着艺术方面去发展。这时,王攀元的画已经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空蒙草原,这既是家乡风景的写照,更象是青年画家苍凉的心境。
中学毕业之后,王攀元同时考上复旦大学和上海美专,他准备进入上海美专的最后决定,又让家中的长辈们给大泼冷水:“我们不给他一文钱,他是无法成行的。”幸好,王攀元第一学期的注册费已经有了着落。同学的父亲借了他五十块大洋,要他毕业后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来还钱就可以了。
离家远行的前一天,家中烧饭帮佣的朱妈自动为他整理行囊,偷偷的说:“这一吊钱是我赚来的工资,你拿去零用。”王攀元感动得抱着朱妈痛哭一场:“人皆有父母,我独无,朱妈也就是我亲爱的妈妈了。”
王同学的甜蜜与悲伤
进了美专,刚好恩师吴茀芝也应聘到那儿任教,吴老师帮他向校长说明了王攀元求学的艰辛,学校特别答应减免他的所有学费。但是,要用五十大洋过一学期的生活并不容易,王攀元只能早上喝点白开水,吃一两个山芋充飢,中午根本无法按时进食,晚上才敢去吃一顿饱饭。有时候实在饿得发昏,名不符实的“王家二少”只好厚着脸去菜市场帮人拉车,换点冷饭,要不就到工厂做点临时工或到街上叫卖报纸。
为了第二学年的学费,形体虚弱的王攀元回到苏北的家中,朱妈问说:“相公!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那时,家中上下人等已经完全对他视而不见,只有朱妈偷偷含着泪水说:“相公你不能为了读书而损毁健康。没有身体什么事都完了。”完全不能自己的王攀元,把“朱”这个字略去,直接叫一声“妈妈!你永远是我的妈妈……”朱杌卮鹚担骸安唬∥矣涝妒窍喙氖陶摺!贝耸保髌土饺酥荒鼙г谝黄鸫罂奁鹄础�
朱妈不断地向家中长辈游说,可惜终无希望。后来是一位看松林的老黄,自动透过朱妈说他愿意借助王攀元一学期的费用,条件也是等他毕业之后按照物价指数偿还。王攀元的学费借贷问题,一直到最后一学期终于弹尽援绝。后来,有位亲友看到他身上的皮袍,就要他脱下来抵押借钱;隔没几天,没有皮袍御寒的王攀元就在零下四、五度的大雪天里,倒卧教室不醒人事。学校将王攀元送到上海红十字医院治疗,医院诊断结果是当时存活率很少的伤寒症。
王攀元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医院连续发出两封电报给家属,第一封说王攀元病情危急,第二封说王攀元已病故请速来善后!苏北老家竟然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医院上上下下为之哗然。
危急之际,有位上海音专的女学生季竹君刚好到医院探友,闻及此事,于是要求护理人员带她到隔离病房。昏昏沉沉之中,王攀元记得季竹君用手帕擦去他面孔上的汗与泪,在他耳边轻声细语的说:“王同学,你现在急需是什么?”王攀元说:“请医生救我,否则我死了,谁来埋我?”季竹君回答说:“王同学,我来救你,我将永远在你身边,万一你不幸死了,我会与你一同埋在土中。”
当下的情境,王攀元在〈浮生往事〉里是这么描述的:“朋友!那个时候我正在昏昏沉沉中与她如此不可思议的对话,她用这两句颇有涵义的哲语攻入我的心灵深处,比任何特效药还来得有效。”就在季竹君的细心照料之下,二十五岁的王攀元竟然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
出院之后,两人开始交往,季竹君还曾与王攀元为将来画下这样的美梦:“将来在西湖桥畔,盖一小木屋,我弹琴,你作画,一起看秋山秋叶,芦花飘荡,群雁南飞,相视到老,永不分离。”在宜兰家中接受采访的王攀元,后续还说了许多季竹君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旁听的人却还是忍不住插了话:“王老师,她都一直叫你‘王同学’,而不是别的称呼吗?”
王攀元很认真的说:“是呀,他都一直叫我‘王同学’。季竹君就是那种女中豪杰,走在时代前面,要为大众服务的人,他都是这么叫我的呀。”回答的同时,大块红晕出现在老先生充满皱纹的满脸笑意上。
永远保有浪漫的情感
王攀元就读上海美专的时候,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是校董,画家刘海粟是校长,校风极为开放。王攀元在美专就学期间,不知不觉地开始将国画的意境融入西画的创作里。当时,留法归来的张弦老师为他奠定下扎实的素描与油画基础,陈人浩老师教他水彩,他还随诸闻韵和潘天寿老师学国画。周末,他继续跑到研究所听潘玉良和王济远老师的美学课程。
美专毕业后,王攀元和季竹君相约一起随潘玉良老师赴法国留学。为了学费与旅费,王攀元只得暂时与季竹君道别,只身回家争取自己应得的家产。几经冲突和百般曲折,王攀元终于争得继承的田产,但是宗族里的长辈却有人公然放话:“谁敢买二少的地,我就毙了他!”王攀元手上的田地一时没有可能变成现钱,因为没人敢买那些地。
旅费没有筹成,卢沟桥的枪声却已响起,王家所处的徐家洪随即落入日人手中。王攀元心系人在上海的季竹君,却因为战争而不能前往相会。王攀元不但去不了法国,连上海也到不了。他和她之间这场如同梦境般的恋情,就这样给战争炸成藕断丝连的时代悲剧。
六十多年来,季竹君总是出现在王攀元的日记与手札当中。他曾在札记里写下“男人都需要某种东西来提高他们的本性,这东西就是:爱慕一个可敬的女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沉默的王攀元实在一直在孤寂生活中,保有着浪漫的情感。
一九四二年,已经三十一岁的王攀元偶遇十七岁的倪月清,当时他对一身土布花衣、纯真秀丽的她留下印象,却在一年后才开始交往。一九四五年,王攀元被日军抓去,隔日就要枪毙,幸得一不知名的壮汉搭救才得以逃脱;王攀元决定放弃一切,带倪月清离开老家。一九四八年,相知相随的倪月清,毅然决定嫁给穷困潦倒的王攀元。隔年,王攀元一家三口随着部队搭船到台湾。
第二故乡的“风台”使人愁
初到台湾,王攀元在高雄港码头当了三年杂工,几次买竹筑屋却都被一次次的台风给吹倒。
“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当地人一直说要小心‘风台’、小心‘风台’是什么意思!”一九五二年,王攀元受堂弟推荐到罗东中学教书,他找到一处无人住的草寮让全家栖身,隔年的“风台”却又将“家”给吹跑。至此,王攀元只能和家人过起居无定所的日子。
月薪不过三百元的王攀元,虽然有罗东中学同仁的相互照应,但是生活还是过得十分困顿。然而,他还是利用夜半的孤寂天籁继续作画、读书、写作,并且以画家传记中所记“你是画家,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你仍是一个画家”来勉励自己。一九五九年,王攀元在罗东农会开了此生第一次画展,各三十幅的水墨与水彩画悉数被买光,轰动一时。但是,偿还借贷之后的王攀元还是两袖清风。
画展隔年,几位画友邀请王攀元共组“兰阳画会”,王攀元一方面痛蠹乙曰嵊眩环矫嬉仓傅家恍┗婊系募记伞R恢钡浇裉欤岬拇笮∨笥讯蓟钩中屯跖试敖煌�
纯朴的宜兰乡亲与学生,一直让王攀元有着温馨相惜的亲蜜感受。“我迁居宜兰已整整五十年头了。尤其对宜兰同胞对我亲切的印象特别深刻,我每次去台北归来时在车窗中遥望着那孤立在海洋中的龟山岛,我就预知道又回到第二故乡宜兰的家了。有时,我乘北宜公路车在车窗中遥望着兰阳平原田野,简直就是我的第一故乡的翻版啊!”王攀元在近期的日记中如此写着。
不过,兰阳平原的风风雨雨却还是没放过磨练王攀元创作心智的机会。一九六二年,波蜜拉台风来袭,王攀元所有画作、日记和书籍都没入草寮家中的积水,全家当下仓惶涉水离家。那段时间,王家屋内屋外都在下雨,雨声点滴落入画家的心头,王攀元遂将自己心目中的画室给取了“听雨楼”这样的称号。
不仅大自然在考验王攀元,生活上的柴米油盐也没放过王家人。
即便倪月清已经接了许多零工来贴补家用,把个秀丽的村姑给磨成风霜满面的母亲。但是,小孩陆续出生所需的生活费用却永远都不够。王攀元在罗东中学教书的时候,他的“瘦”与“不吃饭”是有名的。同事们几乎没看过他中午带过饭盒,他的午休时间总是在报纸堆中渡过;因为,他要将这点钱省下来留待家用。
习惯没有菜的生活
在大陆,王攀元可以说是“富穷”,他在台湾却是“贫穷”,有人在背后甚至就帮他取了个“大穷鬼”的外号。不过,现实的窘迫却不曾损及他的自尊和创作上的向往。每天晚上,王攀元都不忘在灯下忘情的绘画。
一九六六年,透过台北画友李德的促成,王攀元在国际画廊举办了画展,三十二幅水彩全数给来台拍摄电影《圣保罗炮艇》的美国剧组所购去。一般人对于画作售罄应该会感到欣慰,但是王攀元却在惊喜中带着更多的不舍。王攀元画画原不是为了卖画,他很惋惜画廊的作品怎么没有留下一点给自己,这也造成他往后不愿卖画的情结。
台北首次画展所得两万元,王攀元拿去偿还了借款。后来,为了应付日渐长大的孩子所需,王攀元买下这辈子第一栋水泥房,结果购屋所借的十万元贷款,让他花了往后的十几年去慢慢偿还。虽然,王家终于可以不用害怕风台,但是,“大穷鬼”的封号倒是又跟着主人好几年。
“读书、写作、爱情、绘画,四者缺一不可,否则无生活情趣可言。”王攀元一九七○年写在札记本里的随笔,似乎就是他数十年信守的生活守则。一九七三年,六十二岁的王攀元毅然以身体不佳为由申请退休,他希望自己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留给绘画。虽然家庭经济总是在穷于应付当中度过,但是,王攀元对于读书和绘画所需要的时间或金钱投资却从来不会犹豫。
生活拮据的王攀元,有一次曾将身上仅有的一百元中的七十五元拿去买了一本《现代美术史》:和画友吃饭之后,强烈的自尊驱使他争着付账,这又用去了二十一元,扣掉车资三元,他身上只剩下一元给月清买菜。又有一次,王攀元领了评审费二百元,回家前却先转到书店,后来回家时,手里拿的是书而不是等待中的菜,倪月清看到这情景也只好认了。
“反正我已经习惯了。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把钱都这样花掉了,你要我们全家吃什么?可是,反正他还是会继续这样做。算了,习惯了,我后来就习惯了。”王师母在老师接受采访的空档这么补充说明着。
借用绘画表白内心的苦水
“简化它!简化它!奢侈而舒适的生活妨碍了人类的进步,最明智的人,外表虽然穷困,内心生活却再富有不过。”着有《湖滨散记》的梭罗,他这段话几乎就是王攀元的生活写照。倪月清曾经问王攀元退休之后要干什么?“清道夫!”她的先生这么回答。
王攀元太喜欢孤独和简单的生活。他在自己住家旁搭了个小瓦房,安顿之后更全力投入自己的绘画生活。小孙子有一天问王攀元说“你怎么一个朋友都没有?”王攀元指着满屋满床的书本、画册与画作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啊。”同时,他也思索着许多绘画上的重要命题。“中国画最考究形象的洗鍊简约”,王攀元在日记里这么写着:“所谓画尽意在,就是用最小限度的表现手段,获得最大限度的表现效果。换言之,即意到笔不到。”
画布上,经常可以看到王攀元画出的大块天地。
黄绿色调的天地,按王攀元的说法,是童年家乡无边的草原,那时自己没有朋友也没人愿意接近他,他经常独自在草地上自己和自己玩。悲伤飘零的画面,一次次被涂抹到画布上。最常出现在天地之间的是“红衣人”和“狗”,后者是画家从小最不会被嫌弃的伙伴,前者是季竹君永远的化身,因为她喜欢穿着一袭红夹克。
他画的《追日》,狭长形的画面左下角是快要完全落下地平线的红色夕阳,右边四分之一的下方是条拉长身影的黑狗。《思故乡》忧郁的绿黄天地里,右下角有个模糊的红衣女子,看着左上方的晕黄满月。《月如勾》绿黄天色底下有墨绿的色块,右下角的红衣人这次低着头,而左上角的月亮已经如勾隐入云端。
形而上画廊的负责人黄慈美曾凇杜试沧啡诈ぉだ咸煲木绫荆和跖试墓适隆芬皇榈氖滓承吹溃骸懊康碧崞鹜跖试唤钊肆肫鸹嫔夏侵槐寂艿墓罚敕傻哪瘢悦5墓轮郏R6宰乓荒ㄦ毯斓穆淙眨庑┢嗝赖谋硐螅毯恢治难缘妆缑馈J率瞪希录胖皇撬钠剩皇撬娜浚切沃谕獾穆淠铮刈叛挂值娜惹椋晃藜牡南绯睿凰嬗龅墓停徊磺陌凉恰薄�
王攀元的画风里有几个基本的元素与风格,有观众说“每一幅画,都有画家自己梦的存在”,有评论家说“孤寂中却包含着百转千回的感情激荡”。王攀元对于画中悲剧性则有着自己的见解:“绘画一门,就是创作者的心灵反应,脱离了心的表现,就是抄袭。也就是说,我这特殊的痛苦人生,借用绘画来表白我的内心苦水罢了。”

孤独原来不寂寞
一九八三年,王攀元获得“中华民国画会金爵奖”,并受邀参加台北市立美术馆开馆展。虽然王攀元的画作受到国画会和现代美术界的同时肯定,但七十二岁的老画家,却仍然受着债台高筑之苦。他在日记里写着:“对命运,我无法抗拒,但对艺术工作,我的决心总是不变,永不放弃!”
一九八七年,王攀元在台北皇冠艺文中心办个展,有位准备买七、八幅画的收藏家,坚持要买非卖品的《无奈》,然而这幅画却是一位国外回来的模特儿,喜欢他的画而立刻褪去衣服供他作画而成的作品。王攀元坚持“不能将朋友惜才的情份,拿来做买卖”而不愿割爱。结果,收藏家决定一幅画都不要。老画家继续疼惜自己画里的种种感情,继续欠着别人债。
隔年,王攀元的作品获选为台湾省立美术馆的典藏作品。往后数年,他的作品持续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亚洲艺术中心和省立美术馆参展。一九九四年,八十三岁的王攀元在台北形而上画廊举办“孤独原来不寂寞”个展,隔一年又推出《不只是孤独》个展,画家的生活终于有了改善,王攀元终于让自己和家人有了稳定的家。
曾经有朋友劝王攀元,年纪大了,应该轻松一点过活,譬如说,打打麻将过日子,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王攀元事后气着说:“这,实在有够荒唐,竟然叫我去打麻将。我就是年纪大了才要把握时间呀!”
国立台湾美术馆前馆长倪再沁曾经请教过王攀元,究竟是怎样的态度能让他持续创作不辍,王老答曰:“一丝不茍,率性而为!”事实上,王攀元不仅面对艺术和生活的态度保持一丝不茍,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常有非常率性的处理方式。有次,宜兰文化中心有笔一百万元的典藏预算要拿来买他的画,他却一口气送了价值千万的十几张画,要文化中心转将这笔经费拿来鼓励年轻的画家们。当文化中心表示要召开记者会来表扬王攀元时,他却坚决表示,如果要开记者会,他就不捐画了,因为他并不是沽名钓誉的人。
驻宜兰的《自由时报》记者李奎忠与王攀元交往多年,他曾在接受访谈时说道:“我最尊敬他的是,以他今天的声望,他却不曾在宜兰地区形成任何山头或派系。”李奎忠又补充道:“他让我最折服的就是这种表里如一,真诚无伪的文人风骨。”
人生有几个十年?
艺评家谢里法认为王攀元的画作,“在笔触密集松疏之交错中,产生一种因子的游动,使得画面由单纯而繁复,又由繁复而单纯。”王攀元画作中的色彩韵味与幽深的线条趣味,实在需要观赏者透过画作的尺寸规模与真迹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欣赏。
“我画画喜欢广大、空间广大。我做人做事,空间很大。”关于自己为什么总喜欢画大尺寸的画作,王攀元曾这样对师大美术研究所教授王哲雄说。“好话要简短,废话不用多讲,重要的话、有用的话赶快讲,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所以我画画也是这样,越简单越好,我喜欢单纯。”王攀元画作的大量留白,正是他简单心灵的写照,
文艺奖提名委员在提名理由里写道:“王攀元不属于声嘶力竭,摇旗吶喊型的美术运动健将。他的创作实是一个人心灵和宇宙共通精神的凝鍊,其中具有的深沉孤寂,是典型文人精神的展现,尽管他往往以西画作为材质和表现形式。”他将王攀元形容为“不属于声嘶力竭,摇旗吶喊型”的美术运动健将,确实是非常的贴切。
王攀元到了九十岁还是孜孜不倦地作画,还是继续读书、写作和爱人,一如他几十年前所要求自己那样的生活,他在文人精神上面的展现确实已经力透纸背,沁人心灵。“年轻人一定不能随波逐流,要问自己究竟为什么要画画。画画的人要有自我,有自我就会有目标,有目标就会有成功。”这是王攀元在被问到可以给年轻创作者怎样的建议时的答案。
“人生有几个十年?要找到自我,肯定自我,不要虚伪的过活,你一定要多问问自己几次,人生有几个十年?”在北回在线的火车车窗里,看着海上龟山岛的人,心里不断出现王老充满乡音,却一再重复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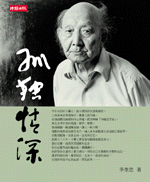
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为忘之交王攀元撰写、整理这样一本“传记型”的书。
与王攀元相识于民国八十年,我在宜兰文化中心工作,编一份地方艺文刊物,采访他,方知宜兰有这么一位人人敬重的老画家。翌年,他在诚品画廊办个展,送我一本《王攀元画集》,我对他那洋溢着孤独氛围、满载情感、在寂寞中踽踽独行的作品,心生一种莫名的感动。
八十二年转行当一名媒体记者,跑宜兰地方新闻。八十六年某天深夜,久久不能成眠,瞥见搁在书堆里的《王攀元画集》,随手拿起来翻阅。这一翻让我陷入王攀元艺术的情境中“无法自拔”,那伫立在天地间的孤单身影、望乡的悠思、想念故人的愁绪、迷蒙的湖水……撩拨着每一根心弦,翻着、翻着,不知晨光熹微。 第二天,我急着想要亲炙画册中那颗孤独、强烈撼动我的艺术心灵。经探询,王攀元离开宜兰市延平路旧居,搬到七张路去了。电话中,我问王攀元能不能找他聊聊,他说:“非常欢迎”。
五年不见,王攀元和我记忆中“一样老”。他告诉我,还记得我这个年轻人,曾向文化中心询问我的去处,得到的答案是我已另谋高就,没想到彼此还能促膝而谈。王攀元那时八十六高龄,对于昔日点点滴滴,皆能记忆犹新、侃侃而谈。思辩和记忆力之强,令我吃惊;一个受尽时代苦难的人,活得如此长寿、坚韧,象是一则传奇。
连续三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探望他一次,和他谈画、谈他的爱、他的恨,他的感恩和他的愤懑。逐渐了解到这位老画家孤独的身影里,隐藏着那么巨大、庞杂、真实、曲折,教人动容的大时代的故事。
王攀元乡音极重,加上嘴里仅剩一、两颗牙齿,混浊的口音,一般人常会听得“雾煞煞”。庆幸的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对这位外省仔语言的理解率却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我常走进时光隧道,听他谈穿着长衫在上海饭馆吃饭、喜欢用袖口抹嘴的朱自清、到上海美专演讲总有一堆女学生环绕的徐志摩,校长兼恩师的刘海粟,原本要带他到法国的潘玉良……这些在文学史、美术史里遥不可及的人物,眼前这位老人家都曾置身“历史现场”!那个战乱的大时代,竟教我心向往之。 王攀元是画坛的独行侠,面对穷困逆境,一身傲骨;功成名就后,却又虚怀若谷。他曾嘱咐我,若在外头听见有人称他为“王大师”,一定要替他澄清说“王攀元不喜欢这样的称呼,因为在他看来,东西方仅各有一位大师,那就是张大千和毕卡索”,他自认要进入大师之列,尚待努力。
王攀元处事的细腻处,常发人深省。多年前诗人#弦主编联合副刊时,有次应邀到宜兰出席救国团的艺文讲座,透过友人朱桥介绍,走访王攀元,并阅得其札记文字,彷如发现文坛新慧星。事后,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联合副刊,制作了一个专题,除了摘取王攀元的札记,也以“独立苍茫自咏诗”为题作专访,并配上一幅油画作品,让在画坛崭露头角的王攀元也在文坛“奔驰了一下”。
对#弦的知遇之恩,王攀元很想以画相赠;又惟恐引发外界“逢迎文坛权贵”的不当联想,只好按兵不动。直到数年前,#弦退休移民加拿大前夕,王攀元赶紧送了一幅八号油画给他。
与我交往,王攀元也小心翼翼,问题出在我的记者身份;宜兰艺文界都知道我最爱写王攀元的新闻,他的大小事情,只要可以报导的,绝不放过。王攀元深怕外界会误以为是他对我下过“功夫”。
有天中午他要我陪他到市区的餐厅吃饭。上车出发前,他找来一顶圆形的黑色宽帽戴上,告诉我说:“和朋友在外头吃顿饭,大家边吃边谈心,原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和你一起吃饭,可就要小心。否则外界传出《王攀元特别请记者吃饭》,就不好了。”下车的时候,他故意将帽子的前缘拉低,左顾右盼进入餐厅,彼时他已八十八高龄,活像个可爱的老侦探。
在餐厅内坐定,王攀元将帽缘拉得更低,嘴巴唸着“希望不要碰到熟人才好”。话刚说完,与我们熟识的宜兰县水利会工程师陈文隆,突然冒了出来,大声的打招呼:“王老师!李记者!”陈文隆寒暄几句走后,王攀元笑着做了结论:“古有明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怎么会忘记了呢!”日后,王攀元邀我出去吃饭,也就不再刻意戴帽了。
王攀元在上海美专读的是西画,却是个全才型的艺术家,文学底子厚实,油画、水彩、水墨皆擅,书法亦不遑多让;其中水墨,除了民国七十六年在台北雄狮画廊举办过一次个展外,即不曾再展出过,原因是宜兰有个画水墨的江苏同乡私下向他表示“你学的是西画,展展油画、水彩就可以,水墨让我来就好”。为了给别人生存空间,自此不再举办水墨展览。八十七年,法鼓山办了一场艺术慈善拍卖会,影视大姊张小燕以廿万元购得一件王攀元尺幅不大的水墨画,经媒体披露,外界讶然“原来王攀元也画水墨”。事实上,所有创作媒材中,王攀元对水墨最有感情,他说,那才真正是中国人的东西。(附图水墨作品:泼墨天色或设色山水) 至于书ǎ晕荒芮朗榉ḿ业牡嘏蹋镀湔婕5幕岵欢唷R死枷厥饭荨⒁死枷厣柚渭湍罟莸任幕步ㄖ呢叶睿蚧嵴估谰蛩扒竽Γ跖试芡窬苷呔×客窬埽荒芡窬苷撸级崆胗讶舜省R蛩衔恍┟怂偷呢叶畲笞郑灰彩怯杀鹑瞬俚丁6源俗龇ǎ涣私馔跖试撸岣械椒艘乃迹私馄湫郧檎撸蚰芑匙盘辶滦模蛭骰咧冢丫Ω恫涣耍粼僭黾铀髯终撸昀系乃攀滴蘖佑Γ慰雒谒嫒绺≡啤�
王攀元的书法到底如何?看过王攀元数件书法作品的宜兰县籍书法家陈政祺指出,王字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点烟火味,或朴拙或老辣,笔墨线条的Q劲直追于右任,内在充满坚韧的生命力,让人爱不释手,百看不厌。
目睹王攀元作画、写字,他的一笔一划、一勾一勒,都有浓浓的“攀元味”,那是一种心灵返朴归真、素拙简约的美丽世界,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艺术学者叶玉静在一篇<大规模的超现实>短文中指出“因为失去面对空白的能力,也丧失面对自己的能力,人们愈来愈依赖各种填充。能够支持廿四小时的忙碌,却无力处理一分钟的孤独。”十九世纪的尼采发现:“人们已经羞于安静,长久的沉思几乎使人的良心产生责备……‘宁可随便做点什么,胜于一事不做’,这条原则也是一根绳索,用来缢死一切教养和一切趣味。”王攀元与其作品正展现了人面对时代和生命之孤独的超凡能耐,若能了解王攀元,懂得欣赏王攀元,相信必能如英国诗人拜伦所写的享受“在孤独中,激起感情万千。在孤独中,我们最不孤单。”
王攀元生活严谨,内心却是向往自由的浪漫主义者。记得他九十岁那年,有天黄昏,在王家二楼与他看画闲聊,老人家坐在一张有把手的藤椅里,夕阳余晖,洒在他光秃的头顶上。这位头戴光环、“话说从前”的老天使,谈起那位生死两茫茫的红粉知己季竹君,讲话的神情、力气,剎那间彷彿回到了青春年少。说到幽微处,眼眶还不禁红湿。我心想,爱情的力量何其巨大,竟能让一个高龄老人这般悸动!虽是迟暮之年,总还要问苍天为何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 王攀元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过去在台北办个展,诗人画家罗青曾以书法文字表达对其作品的赞赏,已故名作家朱西宁专程前往看展,作家小野也曾将女儿李华读国小三年级时看诚品个展的心得报告透过画廊转交给他,王攀元因孤独成性,不擅酬酢,皆未回应。但老来思及,每每引为憾事,老唸着“对不起人家”。去年退休的兰阳女中校长林莲珠,年轻时候服务于宜兰县政府教育局,有次,教育局举办全县学生绘画比赛,王攀元受邀担任评审。午餐时,林莲珠发现他很快就将主办单位发的便当吃个精光,便私下再多给他一个,就因为这个便当,林莲珠退休时也得到了一幅八号油画。
对于艺术本行,王攀元常说:“画家不能只顾画画,不读书”、“作画要有自己的个性,有个性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灵魂”、“画格即人格”。对于人生他亦有自己幽默的洞见:“如果女人要变心,即使台湾银行是你的,也没有用。”、“让男人英雄气短的两大毒药,一是钞票、一是美女。”与他闲谈,话闸子一打开,我随时可以领受他的智慧之语。一般画家画出满意之作,多半会想公诸于世,王攀元却不喜欢让心爱之作“抛头露面”。艺评家黄翰荻针对王攀元的诚品个展,在题为“可怜身是眼中人”的艺评中指出:“王攀元个人以为的真正的好画,由于某些难明的因素并未齐整的出现在台北”。这是不踏进其内心世界,就无法探究的谜。昔日,王攀元自认为好的作品,拿出来示人,屡被批评得一文不值,后来他索性将创作视为“自娱”,又历经逃难,惟恐东西出去就会散佚,养成了舍不得好画或具纪念价值之作,离开身边的习性。
去年,接下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因报社职务忙录,进度有如蜗牛爬步。今年二月,我辞掉服务了近十年的记者工作,才得以放手一搏。王攀元一生的故事情节如大海般浩瀚,若拍成连续剧,精彩度绝不亚于徐志摩的《人间四月天》。
王攀元是个极爱书写的人,写了不少札记,记录自己生活上的所思所感。可惜部分毁于台风、部分损于迁居,我就手头拥有的数件复印件,在书中整理了一个《王攀元札记》单元。凡内容有明确记载年代日期者,均加以附注,付之阙如者,则根据书写的页次推测,让其入列。时报出版公司主编吴家恒看了札记初稿以后,直说:“教人念念不忘”,相信#弦当年也是同样的心情,才会引介王攀元进入联副。
王攀元出版过四本重要画册,分别为民国八十年底诚品画廊的《王攀元画集》、八十一年台湾省立美术馆的“王攀元画展”、八十七年自费出版的《王攀元画集》及九十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攀元追日》。因上述画册图版多所重复,此书特别收录一些未面世的精彩之作,尤其比较少见的水墨和书法,供读者欣赏参阅。
最后,仅将此书献给长我半个世纪,待我如师亦如父的王攀元,愿他的艺术成就,千秋万世,传之永远。 写于民国九十二年四月
百年孤独(节选) ◎文/李奎忠
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王攀元、原本计划与救他一命的女友季竹君偕同潘玉良留学法国,因中日及国共内战爆发,意外落户兰阳平原。他穷困潦倒,为人和性情,如那孤独深沉的画风不被人理解,在本地人眼中他是个“外省仔”,在大陆同乡的眼中,亦是“非我族类”。
王攀元是台湾画坛把艺术创作和孤独画上等号的画家,他尝言:“一个画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体系与风格,那就是孤独。”他的一生与艺术创作可以说就是孤独的结晶,是由亲情、友情、爱情及大时代的动乱等各方面的遭遇凝聚而成。
亲情的孤独
王攀元出身江苏豪门,父亲王汉华对中国音乐情有独锺,是一个琵琶好手。在他三岁时就病逝了﹔母亲则是唐诗宋词的文学迷。王家自王汉华过世后,即陷入庞大家产的争夺战之中,最后由叔父当家,王攀元和母亲从此过着凄风苦雨的日子,备受打压。王攀元十三岁时,母亲病倒离世,成为孤儿。
王攀元考取当时的江苏名校淮安中学,叔婶作梗不愿提供资助,在学费无着的情形下,休学了一年,经佃农协助,终得入学,此后便一直活在为学费调头寸的阴影中。就读上海美专最后一年,感染伤寒重症,已快病危,家人也无闻问,对于医院的电报置之不理。
王攀元在民国六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的札记中写到:“有时想起了家,想起了童年,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真不知道是如何打发的。”而面对亲情的孤独,他在六十八年二月四日的日记中发出了如此动人心弦的吶喊:“来世如再为人,愿能享受父母之爱﹗”
爱情的孤独
爱情的孤独是人间深沉浓烈的孤独,面对真爱却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其苦闷遗憾教人断肠。王攀元与季竹君的意外相逢,意外别离,就象是一则充满遗憾、但美丽的爱情故事。
二十四年,农历九月九日,我与季游西湖灵隐寺,时属深秋,灵隐道旁,落叶纷纷,我与季相对唏嘘,叹人生之几何,而今各一方,悠悠岁月,哭笑不得。季,妳是否仍在人间﹖作梦相见吧﹗(五十八年九月九日)
一个人在爱情上如不能圆满达成,再加上远离天涯,生死不明,到了这个地步,内心是如何的痛苦呀﹗……我们在杭州西冷桥畔,誓言在美专毕业后,在西湖灵隐寺旁,建一小木屋,作为一个乌托邦、安乐乡、归宿地,我们在这里读书、作画、填词、弹琵琶……厮守终身,不与任何人打交道,而今一切已成空想,悲矣﹗月清时常问我“你到台湾来,为什么不拉胡琴,不弹琵琶呢﹖我很喜欢你那套绝技……”我的回答是,不感兴趣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我是无法告诉她的。
今夜梦妳与我拥抱至天明,妳将我带到另一世界……尽情的作画,画我们心灵中之所应画的语言,拥抱、画画、画画、拥抱,直至死去。(五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竹君,妳对水墨画的领悟力特别强,感性力更极佳,今后我很想与妳多在一起闲聊,谈诗、谈文、谈画、谈人生,这是我的希望,而不是命令,..(六十九年八月十六日)
梦想中,如有一个真正爱我,柔情似水的女人,一同读书,一同作画,一同死去,一同埋在土中永远安息,我就不再像一片飘零无依的落叶了。
从札记的心情告白,可以了解到失去季竹君是如何的教他泪枯肠断,以致成为生命中永远的痛。对王攀元而言,爱情的孤独永远没办法用其他东西替代,最多仅是转移注意力的暂时性淡忘而已。尽管物换星移,时移事往,蓦然回首,仍是深深的一道伤口,而这道伤口,在他日后的艺术作品中慢慢的沁出血来。
孤独情深(节选) ◎文/李奎忠
与民国同一年诞生的王攀元年事稍长后,性喜单纯的他,偶会抱怨父亲王汉华在其名字里为他取了“攀”字,笔划多,实在不好写,遂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王后”,笔划简单多了。不过年岁老大的王攀元,却人如其名,果然在台湾画坛“攀元”,以九十高龄荣获国家文艺奖的桂冠,若其父地下有知,出了这么一个儿子,也该含笑九泉了。
王攀元出生江苏世家,他尝回忆:“我家房舍,先祖父时代是仿宫殿式建筑占地数万坪,四周古木参天,后面有一条人工运河,东流入海,门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那辽阔的空间,令人开拓胸襟……好像是一个独立的皇宫,每到民俗佳节,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稚龄时,王家僱请了三、四十名佣人,负责烧饭、打扫及门禁等各种杂务。老家常有狐狸和蛇类出没,老祖母一再叮咛小孩子不能打狐狸,她认为家运旺才会引来狐狸聚集。
老家�